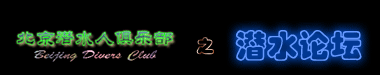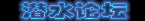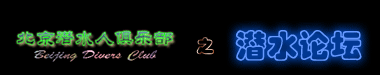|
|
  共2 页 第1页 (10条跟贴/页) 共2 页 第1页 (10条跟贴/页)
  |
|
|
|
|
 |
海底打捞 |
 |
2005-11-10 21:41:35 |
|
|
主题:招聘海底打捞人员
内容:
我是福建人,前一段时间在我们老家发现了俩艘古代沉船,上面有许多的南宋时代的瓷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我联系.QQ418661252.电话.013305041199
|
|
|
|
|
|
|
 |
richard |
 |
2005-11-11 01:35:19 |
 |
蓝色星球 |
 |
 |
|
|
|
|
|
|
|
|
 |
海底打捞 |
 |
2005-11-11 09:41:14 |
|
|
|
|
|
|
|
|
 |
more-or-less |
 |
2005-11-11 11:56:26 |
 |
沙姆沙伊赫 |
 |
 |
|
|
|
|
|
|
|
|
 |
海底打捞 |
 |
2005-11-11 22:44:47 |
|
|
|
|
|
|
|
|
 |
乌龙八戒 |
 |
2005-11-11 23:49:59 |
 |
北京 |
 |
 |
|
|
跟贴:听起来好像挺诱人,但是我们学潜水的目的好像不是这个吧,在这里发这个,不知道回有几个人响应!
|
|
|
|
|
|
|
 |
BG1NBC |
 |
2005-11-12 22:46:55 |
 |
李家凡 |
 |
13945000001 |
 |
北京 |
 |
 |
|
|
跟贴:你3,我7,公安你负责!!
不会是你在竭石吧?呵呵,成交吗?
|
|
|
|
|
|
|
 |
richard |
 |
2005-11-13 02:13:29 |
 |
蓝色星球 |
 |
 |
|
|
跟贴:下面的文章比较长,请耐心看完:
(摘自: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7日12:26 南方周末)
□ 本报记者 李海鹏
10月23日,李滨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上看到了一种康熙中期青花大瓷盘,直径超过40厘米,标价8万元人民币。这位中国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馆员随后告诉这个中心的主任,中国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那就是他们刚刚发掘过的沉船上的被盗文物。
这艘丢失了文物的沉船,就是中国水下考古队在过去的100多天里一直在紧急抢救的福建平潭“碗礁一号”。
从反盗捞开始
在“碗礁一号”沉船水域,25艘渔船狼奔豕突,左右盘旋,忙来忙去,场面混乱得如同一场100年前的海战。
6月24日,福州市平潭县屿头岛,一位林姓渔民在附近的碗礁海域捕鱼时捞上了几件古代瓷器。这在当地算不得新鲜事,碗礁得名就是因为附近海域常常有瓷器出水。不过这一次他却没有像祖辈那样把它们扔回海里。当天,他穿上潜水装备下海查看,发现有一艘古代沉船半掩在淤泥之中。
他捞上来更多的瓷器,并把消息散布出去。很快,屿头岛上的渔民们加入到了打捞古代财宝的行列中。
边防派出所的警员获得消息,到一位有嫌疑的渔民家中搜查,可惜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只找到了7件“疑似”文物。
6月25日,这位渔民家中的最破和最旧的7件瓷器被送到福建省文物局鉴定中心。27日,得出鉴定结论:1件普通文物,5件文物标本,1件非文物。
7月1日下午,福州市考古队队长林果匆匆赶到屿头岛上的边防派出所时,一看到警员们从渔民家里搜查到的被盗捞的青花瓷器,他就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无奈地迟到了。“这是惊天大发现啊,全是我们做梦都要找的东西!”他马上打电话给张威,“你赶快过来吧!”
当天,国家文物局就下发文件,要求制止盗捞行为。不过如此快速的反应,这也只能算作亡羊补牢之举。沉船上的康熙年间青花瓷器,已被大规模盗捞达一个星期之久。据张威事后估计,文物至少损失了50%,即16000件左右。
“我只能说令人遗憾。因为拿到的几件文物不够好,沉船就被扔在那儿了。”3个多月后,林果说,“我们不能仅凭少数文物判断一艘沉船的价值,就像不能用一根头发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一样。”
“其实这是一个程序问题,文物鉴定仅仅是判断遗址价值的辅助手段,而不是主要依据。”张威说,“遗址的发现处理,应该依照地方文物部门上报国家文物部门的程序,而不是在地方上平行地交由鉴定中心来判断。”
林果得到消息是在6月30日上午,队中的福建省考古所所长栗建安接到下属的一条手机短信,主要内容是:“在平潭县水下发现一艘古代沉船,放大量瓷器,现在很多村民都在拿。”当时,栗建安正与林果一道,作为国家博物馆组建的中国水下考古队成员,在福建漳州东山县做“福建沿海调查”。
他们意识到这件事或许蕴藏着机会。林果到省市文物部门询问此事,福州市文物局局长王华南告诉林果,去与福州市文物局的副局长刘亮商量此事。刘亮也表示自己不清楚此事,不过这位副局长做出了一个很容易做出而且非常明智的决定:“ 我们的考古队先介入一下。”
7月1日,林果率领的一支由7人组成的水下考古小队到达了屿头岛。在西码头上,他就觉得事情不对。码头上挤了七八条船,聚集了50多人,最不寻常的是,每艘船上都有潜水设备。
出海不远,他们就听见了马达的阵阵轰鸣,看见海面上飘动着浓浓黑烟。在“碗礁一号”沉船水域,25艘渔船狼奔豕突,左右盘旋,忙来忙去,场面混乱得如同一场100年前的海战。渔船上都有潜水设备,海面上漂着用于定位的浮标。
屿头岛已经“全民皆捞”。附近区县能够雇来的潜水员全被雇来了,更多的潜水员则从广东、浙江、安徽、上海甚至山东来到这个小岛。这些人中有的来自专业打捞公司,另外一些人则是“票友”性质的旅游潜水教练,甚至还包括了几个在渔场里捞鲍鱼和海参为生的捞海仔。
由于成本不菲,渔民们各自结成了暂时性的“夺宝股份公司”,由多位渔民以股份制形式负担盗捞成本并按比例瓜分所得。在风气最盛的28、29日两天,往日宁静的屿头岛宛如传说中的黄金岛,盗捞者们精神亢奋,各式渔船穿梭往来,日夜不停,文物开始大规模地打捞出水,损坏丢弃不计其数。不时有文物贩子上岛,以数百至1000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瓷器。
在前些年“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的发掘过程中,也曾发生类似情况,不过当时在有关部门的查禁之下,渔民的盗捞行为很快就被遏止。这一次却大大不同,资讯传播的发达和民间文物市场的畅通,使得当地渔民对于自己将会收获什么一清二楚。“没办法,”张威感慨说,“时代不同了。”
6月30日,屿头乡贴出禁止在碗礁海域打捞沉船文物的通告。就在当夜,盗捞仍在继续,因供氧设备出现故障,一位32岁俞姓潜水员深夜溺毙。这些潜水员大多使用危险的气泵供氧设备,以延长在水下的停留时间。这种方法之古老,与1848 年人类第一次进行水下考古时别无二致,那时为了搜寻瑞士湖中的居民遗址,洛桑博物馆的馆长在小船上用手动压缩机为潜水员输送空气。
在记者得到的一份上报给福建省文化厅的报告草稿中,当地文物部门描述说:“水下沉船海域不仅出现了明抢暗偷、黑吃黑、非法武装盗抢的恶性事件,导致许多珍贵文物流失走私,更有甚者出现村民集资参与盗捞的现象。”
7月2日,尽管国家文物局还不能马上批准发掘执照,中国水下考古队已经开始从东山县沿海向屿头岛整体迁移了,他们不得不再次从一次课题性发掘转到一次抢救性发掘中来。作为考古人员,他们的目的不是财宝,却注定要面临财宝带来的烦恼。
? 6月24日,福州市平潭县屿头岛,一位林姓渔民在附近的碗礁海域捕鱼时捞上了几件古代瓷器。这在当地算不得新鲜事,碗礁得名就是因为附近海域常常有瓷器出水。不过这一次他却没有像祖辈那样把它们扔回海里。当天,他穿上潜水装备下海查看,发现有一艘古代沉船半掩在淤泥之中。
他捞上来更多的瓷器,并把消息散布出去。很快,屿头岛上的渔民们加入到了打捞古代财宝的行列中。
边防派出所的警员获得消息,到一位有嫌疑的渔民家中搜查,可惜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只找到了7件“疑似”文物。
6月25日,这位渔民家中的最破和最旧的7件瓷器被送到福建省文物局鉴定中心。27日,得出鉴定结论:1件普通文物,5件文物标本,1件非文物。
7月1日下午,福州市考古队队长林果匆匆赶到屿头岛上的边防派出所时,一看到警员们从渔民家里搜查到的被盗捞的青花瓷器,他就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无奈地迟到了。“这是惊天大发现啊,全是我们做梦都要找的东西!”他马上打电话给张威,“你赶快过来吧!”
当天,国家文物局就下发文件,要求制止盗捞行为。不过如此快速的反应,这也只能算作亡羊补牢之举。沉船上的康熙年间青花瓷器,已被大规模盗捞达一个星期之久。据张威事后估计,文物至少损失了50%,即16000件左右。
“我只能说令人遗憾。因为拿到的几件文物不够好,沉船就被扔在那儿了。”3个多月后,林果说,“我们不能仅凭少数文物判断一艘沉船的价值,就像不能用一根头发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一样。”
“其实这是一个程序问题,文物鉴定仅仅是判断遗址价值的辅助手段,而不是主要依据。”张威说,“遗址的发现处理,应该依照地方文物部门上报国家文物部门的程序,而不是在地方上平行地交由鉴定中心来判断。”
林果得到消息是在6月30日上午,队中的福建省考古所所长栗建安接到下属的一条手机短信,主要内容是:“在平潭县水下发现一艘古代沉船,放大量瓷器,现在很多村民都在拿。”当时,栗建安正与林果一道,作为国家博物馆组建的中国水下考古队成员,在福建漳州东山县做“福建沿海调查”。
他们意识到这件事或许蕴藏着机会。林果到省市文物部门询问此事,福州市文物局局长王华南告诉林果,去与福州市文物局的副局长刘亮商量此事。刘亮也表示自己不清楚此事,不过这位副局长做出了一个很容易做出而且非常明智的决定:“ 我们的考古队先介入一下。”
7月1日,林果率领的一支由7人组成的水下考古小队到达了屿头岛。在西码头上,他就觉得事情不对。码头上挤了七八条船,聚集了50多人,最不寻常的是,每艘船上都有潜水设备。
出海不远,他们就听见了马达的阵阵轰鸣,看见海面上飘动着浓浓黑烟。在“碗礁一号”沉船水域,25艘渔船狼奔豕突,左右盘旋,忙来忙去,场面混乱得如同一场100年前的海战。渔船上都有潜水设备,海面上漂着用于定位的浮标。
屿头岛已经“全民皆捞”。附近区县能够雇来的潜水员全被雇来了,更多的潜水员则从广东、浙江、安徽、上海甚至山东来到这个小岛。这些人中有的来自专业打捞公司,另外一些人则是“票友”性质的旅游潜水教练,甚至还包括了几个在渔场里捞鲍鱼和海参为生的捞海仔。
由于成本不菲,渔民们各自结成了暂时性的“夺宝股份公司”,由多位渔民以股份制形式负担盗捞成本并按比例瓜分所得。在风气最盛的28、29日两天,往日宁静的屿头岛宛如传说中的黄金岛,盗捞者们精神亢奋,各式渔船穿梭往来,日夜不停,文物开始大规模地打捞出水,损坏丢弃不计其数。不时有文物贩子上岛,以数百至1000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瓷器。
在前些年“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的发掘过程中,也曾发生类似情况,不过当时在有关部门的查禁之下,渔民的盗捞行为很快就被遏止。这一次却大大不同,资讯传播的发达和民间文物市场的畅通,使得当地渔民对于自己将会收获什么一清二楚。“没办法,”张威感慨说,“时代不同了。”
6月30日,屿头乡贴出禁止在碗礁海域打捞沉船文物的通告。就在当夜,盗捞仍在继续,因供氧设备出现故障,一位32岁俞姓潜水员深夜溺毙。这些潜水员大多使用危险的气泵供氧设备,以延长在水下的停留时间。这种方法之古老,与1848 年人类第一次进行水下考古时别无二致,那时为了搜寻瑞士湖中的居民遗址,洛桑博物馆的馆长在小船上用手动压缩机为潜水员输送空气。
在记者得到的一份上报给福建省文化厅的报告草稿中,当地文物部门描述说:“水下沉船海域不仅出现了明抢暗偷、黑吃黑、非法武装盗抢的恶性事件,导致许多珍贵文物流失走私,更有甚者出现村民集资参与盗捞的现象。”
7月2日,尽管国家文物局还不能马上批准发掘执照,中国水下考古队已经开始从东山县沿海向屿头岛整体迁移了,他们不得不再次从一次课题性发掘转到一次抢救性发掘中来。作为考古人员,他们的目的不是财宝,却注定要面临财宝带来的烦恼。
时间之战
他们本可以等待海水在明年3-6月份转回清澈,如果没有发生大规模盗捞的话。但是等待是不可能的。
在7月初,平潭县公安局、边防大队和福建省边防总队海警一支队控制了沉船水域,盗捞者的潜水员被撵走了,考古队的潜水员来了。7月2日,顺着盗捞者留下的浮标,水下考古队员直接潜到了沉船附近,确定GPS位置,进行了第一次水下摄影。3日和4日,进行初步水下调查并出水少量瓷器。由于事情紧急,4日当天考古队就做好了光盘。5日,林果带上光盘,乘飞机到北京汇报,国家文物局的几位局长都等在会议室里。
7日,国家文物局下达正式通知,马上对“碗礁一号”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12日,发掘执照批下。总额超过700 万元的发掘经费由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博物馆共同垫付,将来会由财政部埋单。
7月10日,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开始。国家博物馆临时组建的中国考古队全员来到屿头岛,仍然人手不足,只好征调了全国所有的可用人才,包括正在中国水下考古第三期培训班学习的学员。
水下遗址发掘与田野遗址发掘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水下考古队员们把最初的一段时间用于调查,即定位、测量、照相和摄像等等。他们取下了盗捞者设置的浮标——它用一个铁耙子勾在沉船的船舷上——改用自己的铅坠浮标,然后按照安全规则,顺着浮标下的入水绳成对下水。
如果不必与盗捞者争夺时间空间的话,单就工作程序而言,水下考古工作就像是一种优雅有趣的积木游戏。最初几天,潜水长张勇带领队员们在沉船上方布好用于标明方位的基线,然后按照正南正北的方向,用不锈钢管或绳索设置20厘米× 20厘米的“探方”,即用于考古发掘的单元格。每隔20厘米用红色胶布做一个记号,以便水下辨识。这是他们的水下魔方。
在这一阶段,队员们应该尽量保持水下遗址的原貌,不过原貌早已不复存在。早在第一次下水后,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过来支援的队员冯雷就对队友们说,自己又想笑,又想哭。“就考古来说,这是难得一见的好船,”如今他回忆说,“ 可是当时水下的情况真是惨不忍睹。”
在水底,破损的瓷器四处散落,每处断口都闪烁着簇新的白光。这还只是新近发生的破坏。在船尾靠西的位置有一处海底的泥沙特别松软,看来是在前几年被人炸过,船尾因此已经完全消失。
幸运的是,考古队遇到了良好的水文情况。7月初,这片海域的水温在28℃左右,流速30cm/秒上下,能见度也在一米至两米之间。水深14米,海浪冲不到沉船,海底坚硬,海流缓慢。如此理想的水下环境,甚至让在恶劣环境中发掘过“南海一号”沉船的冯雷大有陶醉之感。
白天,考古队员们忙于调查。晚上,他们则租用码头上的渡轮到沉船海域监视动向。有几天夜里,有装载着潜水设备的渔船在附近抛锚,甚至有一艘船已经触碰到了海警部门在周围海面上布下的警铃。渔船上的盗捞者与队员们对峙,时停时走,不敢下水,却报复性地不让队员们睡个好觉。
平静仅仅持续了10天。7月20日,“海棠”台风来了。这是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水下考古的黄金季节是3-6月,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台风这种气象灾害——它会耽搁发掘的时间,又搅动海水,大大降低海底的能见度。然而对于这次发掘来说,它带来的坏处还远不止这些。
“海棠”平息之后,连日来困在岛上避风的考古队员们再次下水,却发现瓷器又有了新的丢失和损坏,沉船的隔舱板被掀开了,基线被扯乱,水底还遗留着用来系浮标的石头和渔民们的耙子。盗捞者们不仅敢于在考古队和海警都不得不畏惧的台风中出海,而且敢于在台风中下水。
在为期100天左右的发掘过程中,福建水域共遭遇了5次台风。沉船发掘工作因此时断时续,盗捞却因此时有发生。渔民们也有损失,在“海棠”台风期间,一艘冒险的渔船因此沉没在附近海域。
“我们不得不加快进度,”林果说,“本该进行得更充分的调查工作只好提前结束。”考古队感到最急迫的,是要把瓷器尽快打捞出水,以断绝盗捞者的觊觎之心,尽管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严格遵守考古发掘的原则。
“海棠”台风之后,沉船水域的能见度急遽下降,以后几个月中始终维持在10至20厘米左右,再也没有明显好转过,最低时几乎为零。对于“寻宝”型的打捞者来说,浑浊的视野并不是问题,他们摸到文物提出水面就可以了,可是对于水下考古队员来说却几乎是一场灾难。
如果只是打捞深海沉船,那么只要在沉船地点放下蒸气爪钳,夹住残骸用力拉上水面就可以大功告成。水下考古的工作,却决非如此简单粗暴。水下考古的科学范畴,包括古瓷器研究、航海史研究、造船史研究、海上贸易史在内的各考古领域,因此收集沉船上的各种信息而非捞出瓷器,才是发掘工作的要义所在。当能见度过低时,信息收集的成效自然大打折扣。
在台风来临前,队员们可以很从容地在水下铺好特制的硫酸纸,按照1∶20的比例,用铅笔绘下“探方图”。在台风之后,他们只好在一片混沌中摸上一通,靠触觉判断方位、形状、比例,回到船上后靠记忆画下图纸。
实际上,他们本可以等待海水在明年3-6月份转回清澈,如果没有发生大规模盗捞的话。
等待是不可能的。“在盗捞最疯狂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海岛上买不到鱼吃,”林果说,“渔船都去捞宝贝去了。”
广东省阳江海域的“南海一号”宋代商船,2002年正式发掘,中国水下考古队事先准备了10年,针对沉船海域进行了15850人次的潜水勘察,累计达50万工时。为了发掘“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遗址,这个考古队先后进行了6次试验性发掘,甚至将沉船遗址整体圈在拼接框架之内。相比之下,“碗礁一号”沉船的发掘工作却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又不得不在艰难的情况下继续。
幸好,这仍是一次收获颇丰的考古行动。“船上的东西真是好,”冯雷说,“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觉得特别震惊。”
吾华之瓷
“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对于这次发掘出的瓷器,张威有一个简明的评价:“已探明的水下遗址中最好的。”
在南方夏季的天气、潮汐和水流的影响下,水下考古队员们可以用于下水作业的时间微乎其微。每次下水他们最多可以停留40分钟,每人每天平均下水3次。在深海中,队员们的意识都很模糊,注意力难以集中,因此必须在潜水之前就准确做好全部计划,入水后惟盼尽快完成。
船体和文物的一部分都埋在淤泥之下。最初几天,在打“水炮”时——用高压水枪冲开覆盖沉船的坚实海泥——队员们还从容不迫,等待浊水漂去时也好整以暇。发掘到第10天以后,情况急转直下,每次使用气泵抽泥之后,他们都焦虑难耐,因为泥流使得一切都模糊不清。
水下考古中的气泵相当于田野考古中的手铲,没有它就难以使工作向下方延伸,如今队员们却不得不经常性地放弃掉它。在漫长的盲人摸象式的考察过程中,队员们发现沉船残长14米,残宽3米,残高1米,甲板以上缺失,头部和尾部缺失。除此之外,收获并不多。原本清晰划分的舱位,在能见度下降后也难以重新找到。
直到9月20日前后,能见度才终于有所恢复,摄影、绘图等工作得以比较正常地进行。这时,瓷器可以大规模打捞了。当一个水平层面的瓷器出水后,“探方”调查继续,摄影、摄像、测绘,新一轮的发掘程序再次启动。
青花瓷器,始终是“碗礁一号”沉船的焦点所在。流传在中国考古界的一句俗话是,“一艘船十个墓”。船舱容积的无可匹敌,代表着文物数量种类的蔚为大观。没有人能回避得了文物的经济价值。
到发掘工作阶段性结束时,包括海警和边防从民间收缴回来的1287件文物在内,“碗礁一号”沉船发掘共收获了 16000件瓷器整器和碎片主体。随着瓷器的陆续出水,鉴定工作也依次展开。专家们认定,大部分瓷器属青花类,色泽优雅,胎质匀实,无官窑款识,为康熙年间景德镇民窑精品。
9月19日,适逢一年中最猛烈的天文大潮期间,考古队员对各个船舱进行了抽泥和清理,测绘出新的数据。发掘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他们的计划是查看沉船的船底形状,并清理船周围淤泥中的散落文物。
这一天,在“东六舱”,“克拉克瓷”出水了。水下考古人员发现了几摞完好无损、绘有花朵植物图案的花口青花大瓷盘,口对口或底对底紧密摆放,显然维持着300多年前装船时的原始姿态。由于这块区域海底泥沙比较坚实,队员们先清除上面的泥沙和周围的杂物,然后分步骤慢慢取出了55件青花瓷盘。
出水后,瓷器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华莎发现,这些瓷盘上所绘图案为地中海地区的花卉植物,而非中国瓷器传统图案中的本土花卉。她据此推断,这是一批由欧洲商人特别定做的瓷器。
“这种花卉图案具有典型的欧洲风格的青花瓷器,也就是当年欧洲人所称的‘克拉克瓷’,”陈华莎说,“‘克拉克瓷’也就是中国青花瓷器在欧洲的叫法,其实专指这种深得欧洲王公贵族喜爱的外销瓷。”
同一时期,沉船中还出水了一些筒花觚、高足杯,均按照欧洲习惯,加有盖子,甚至还有一只精巧的欧式的餐桌小花瓶。20日,在初次发掘的“东四舱”,队员们又发现了几个被半埋在泥沙当中的硕大的青花瓷罐。出水后发现,其中一个瓷罐高约60厘米,为康熙年间最为流行的“将军罐”。这只将军罐上绘有装满鲜花的花篮,并有一个“福”字,按照中国瓷器的寓意命名,为“万花献瑞”款式。另外两个瓷罐,一个为青花瓷罐,一个为五彩瓷罐,均为图案精美的瓷器佳作。
出水的大多数瓷器都光洁如新。“流失的部分瓷器如果放到市场上,买主最初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康熙年间的东西,” 张威说,“因为看上去太新了。”不过可惜的是,由于一些五彩瓷器的釉彩分布与青花瓷器相反,为釉上彩,即色彩被描绘在釉层外面,经过300多年的海水浸泡,已经永久性地失去了光彩。
至今,“碗礁一号”已出水16000件瓷器,初步统计有50多种器型,100多种纹饰。陈华莎在鉴定后认为,全部瓷器来自景德镇,其中50%左右的器物采用高质量的高岭土烧制而成,工艺水平并不亚于官窑。
“事实上由于生产能力不够,为了完成宫廷交付的任务,当时的官窑也有向一些民窑定做某些瓷器然后加上官窑的款识的做法,”林果说,“这说明,部分民窑的生产质量并不输给官窑。”
一件绘着和官窑相似龙纹的瓷器,隐约证明了他的观点。根据民窑能够使用被称为“御土”、“官土”的高质量的高岭土烧制瓷器这一前提,陈华莎认为,因此可见当时的政府为了出口已经开禁了“御土”的使用。
对于中国瓷器考古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发现。康、雍时期的青花瓷器为中国瓷器艺术的顶峰之作,《陶雅》说:“ 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另外,“景德镇外无青花”的说法又证明着景德镇青花瓷的至尊地位。对于这次发掘出的瓷器,张威有一个简明的评价:“已探明的水下遗址中最好的。”
文物精美固然令人欣喜,如何保护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相对金属、竹木等材质的文物,瓷器的保护要容易得多,不过经过300多年海水浸泡的“碗礁一号”瓷器一样面临着种种危险。按照程序,每打捞上一筐瓷器,考古队员都会立刻用淡水中浸泡,以使文物脱盐。这是一份看似简单却难以做到最好的工作。
“表面上看瓷器光洁如新,似乎没有受到什么腐蚀,”张威说,“其实盐分会一直渗透到瓷器里面去,甚至穿过釉彩进入瓷胎。”
要做到彻底的脱盐,就需要把这些瓷器在淡水浸泡数月之久,这一过程看起来难以实现。以瓷器数量的16000件之巨,到哪里找那么大的水池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问题。如果脱盐不净,瓷器会渐渐损坏,在“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文物中,已经有部分瓷器因为盐分外渗出现了釉层凸起的问题。
现在,考古报告还未编撰,考古专家们的工作还在破解沉船之谜的阶段。“按照制作工艺判断,这次出水的瓷器绝大多数是清康熙中期所制。”栗建安说,“不过另外一些瓷器却明显为清康熙早期的。为何同批货物中会有不同年代的瓷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揭开谜底。”
另外一方面,出水瓷器中的50%质量平平,其中包括一座欧洲人不可能会欣赏的观音像。有考古队据此推测说,船上的瓷器或许并非销往单一地区。精美的克拉克瓷应该是销往欧洲,质量一般的瓷器则可能是销往东南亚。
对于水下考古学科来说,这都是应予破解的谜题。在瓷器的鉴定基本完成之后,张威们必须回答这艘船是怎么回事。
最美的一艘沉船
这艘沉船究竟是远洋船还是转运船,被看作是福州能否被当作“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新证据。
到9月下旬,“碗礁一号”发掘工作已经阶段性结束,即除沉船本身的打捞之外,摄影、摄像、测绘等调查工作和打捞、保护、清理等文物打捞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对于遭到盗捞,以及抢救性发掘受到的时间限制,中国水下考古队颇感遗憾。张威觉得,如果自己当初对这次发掘的预期值为100分的话,事实上只收获了80分,而林果则认为他们只达到了75分。
现在他们只好期望,对这艘木质沉船本身的进一步考古能够挽回一些分数。这还需要新的经费。
考古队员已对沉船的龙骨进行了探摸测绘。龙骨暴露在水中的部分长1.45米,周长约77厘米,直径约22厘米,厚26厘米,延伸到船板下面,并与船板拼接成一体。根据它的大小,张威推断,沉船的长度在18至20米间,“不太大 ”,以300多年前的中国造船水准来看也只属于中等大小的船只,应为用于近海航行的运输船。
考古专家们大多倾向于同意张威的意见。他们推测,沉船的身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它从景德镇出发,沿水路至长江并出海,在前往福州、泉州或广州的途中沉没;另一种是它的目的地为澎湖列岛,林果按照当时的历史资料估算,当时也许正有一艘西班牙商船在那里等待着这艘转运船的到来。
潜水长张勇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即沉船是一艘中距离的远洋船,或许可把瓷器运抵越南等地。他的依据是,人们曾在越南海域发现类似的中国古代沉船。“这艘船也许是到东南亚去给前往欧洲的大船送货。”张勇说,“这么大的船,如果沿近海航线航行的话,到达东南亚也并非没有可能。”
除了船体大小之外,船的形状值得研究。福建省一些学者猜测的是:它是不是尖底的“福船”,即明清两代的福建一带所造船只?这一点现在还无法判断。张勇说:“我觉得我已经触摸到了船底板,但那是不是船底板,现在还不能定论。”
另外,专家们正在勾勒这艘沉船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之线。以往,这条中欧贸易线路的起点往往被认为是广州、泉州,而这艘沉船究竟是远洋船还是转运船,则被看作是福州能否被当作起点的新证据。
另外一些发现暂时看起来还没有太大价值,比如在船舱中发现的4件日常小器物,分别为一个残留部分墨迹的不及巴掌大的小石砚、一个小罗汉雕像、一个陶制的龙头以及一枚铜钱。林果说,考古如破案,文物如物证,其价值一时很难判断,这些东西或许也会有显现其重要性的一天。
现在最没有疑问的一点是,沉船本身的打捞已经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按照考古操作规程,考古队员本该给它的每个部件编号,以便打捞后重新组装、恢复原貌。不过由于盗捞造成的破坏,船体严重损坏,准确地进行编号已无可能。张威描述说,有些部位已经七零八落。
“沉船是否打捞,还要向国家文物局请示。不是完全不能打捞,但是难度很大。”张威说。
除了“碗礁一号”之外,还有一些沉船正在附近海域渐渐走向毁灭,有很多人在捞取宋元至明清时期的瓷器文物。
“别在屿头岛上问文物的事情,”附近东珠村的一位村民对记者说,“小心捞了文物的人恼火。”
林果曾对当地文物部门人员描述,少数盗捞人员配有武器,还曾有蒙面人在盗捞现场出现。另有水下考古队员说,在海警、边防人员在海上采取方法制止盗捞时,曾有人用砖头还击。在水下考古队前往莲峰村海域调查时,3艘渔船正在盗捞,其中一艘橡皮快艇绕考察船飞驰示威。
不过,考古队员们很了解,盗捞者们本身也只是偷盗者而非天生歹人。“加强约束的话,都是好人。”冯雷说。
事实上,屿头岛上的参与集资盗捞的渔民们远非都能大发其财,雇佣潜水员的价码高到了非理性的地步,导致很多人赔掉了本钱。冯雷曾看到乡卫生院在抢救一个服毒者,渔民们说,他走上绝路就是参与集资盗捞蚀本所致。
不过,在屿头岛,在全国沿海的一些地方,盲目和冲动仍在继续。
幸好,最美的一艘,他们已经得到了。
“‘碗礁一号’是最好的,”张威说,“这真是好运气。”?
|
|
|
|
|
|
|
 |
richard |
 |
2005-11-13 02:25:31 |
 |
蓝色星球 |
 |
 |
|
|
跟贴:还有。
出处: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9日02:42 海峡都市报

|
|
|
|
|
|
|
 |
cy |
 |
2005-11-15 00:01:59 |
 |
中国北京 |
|
|
跟贴:补充几张南方周末文章中的照片:

考古队员正在检查派出所收缴的沉船文物取 李滨/摄

水下文物 李滨/摄

|
|
|
|
|
|
|
 |
菲林同学 |
 |
2005-11-15 15:41:23 |
|
|
跟贴:撩开“克拉克瓷”神秘的面纱“转自:人民网”
明末清初有一种装饰奇异的青花大盘,其盘内壁为连续放射状的各式开光,盘心绘主题纹样,整个布局繁缛华丽,好似盛开的芙蓉花,这种瓷器欧洲人称为"克拉克"瓷,日本人称为"芙蓉手",其多见于国外收藏,影响遍及亚、非、欧、美等广大地区。德国赛尔郎德、美国纽约艺术博物馆、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土耳其的伊斯坦保、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等博物馆都有收藏。这种大盘是当时重要的出口瓷。主要是江西、福建等地生产,另外,日本、德国、伊朗、荷兰、英国和西班牙等国都有仿制。
另说,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瞩目。 无独有偶。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景德镇或武昌所产的青花瓷。
20世纪90年代,一个令国内外陶瓷界欣喜万分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对福建平和南胜、五寨明清古窑址的调查与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烧造国外所谓“克拉克瓷”、“汕头器”的窑址和销往日本等国的实物标本。众多的目光顿时投向平和这个平素不为人所知的闽南山区县。
在平和县博物馆“古陶瓷展览馆”,琳琅满目的古陶瓷标本中,以青花瓷器和“交趾香合”(素三彩香合)最为引人注目,青花瓷器装饰图案各异,大的有脸盆一般,“交趾香合”则小巧玲珑,可赏玩于手掌之中,据说此物与日本茶道联系紧密,一般用于盛放调料,由于制作精美,造型多样,也作为工艺品,为王公贵族所争先收藏。
目前在平和境内发现的以南胜、五寨一带为主的古民窑数以百计,它们建造于临溪的山坡上,形成“十里长窑”,可以设想,这些规模不等、生产花色品种相近的窑口同时开足马力,日夜生产,火光映红花山溪,场面该是何等壮观,产量该是何等可观。
据日本淡水出版社出版的《形物香合》一书图录看,日本收藏的许多瓷器与平和田坑窑形状一致,尺寸大小相近,如龟形、鸭形、鸟形、南瓜形、蛙形香盒等。至今日本有田陶业公司仍保留许多田坑窑制瓷技术和传统工艺。“从传承关系看,平和明清时期的制瓷技术应该是第二代,景德镇是第一代,日本的有田陶业公司是第三代。”
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到任的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组织民间生产烧制参与市场竞争。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它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以平和南胜、五寨窑址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民窑,地处九龙江支流上游,临溪依山而建,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可直达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花山溪流经之地,皆为丘陵盆地,河面展宽,水流平缓,非常适宜水路运输,从南胜、五寨至月港,仅需一天航程。 值得一提的是,平和外销瓷业的迅速崛起与漳州月港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入明,素有“东方大港”美誉的泉州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月港,尤其是明正德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不但远远超过福州港,而且也超过广东港。到了明万历年间,月港的对外进出口发展到最高峰。平和盛产的瓷器正是此时源源不断地通过商船远销世界各国。
有关专家指出:东南沿海贸易陶瓷的生产是在景德镇窑的兴衰起伏中和海外对中国陶瓷需求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的,兴起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平和瓷业就是典型之例。
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据史料记载,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7世纪的80年间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这样大量的瓷器,等级不一,而且仅靠处于困境中的景德镇窑是难以承受的。西方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民窑,当然更希望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以减少运输之苦和搬运过程中的大量损坏。也就在此时,明万历(1573—1620)年中,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于是,福建沿海民窑就成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南胜、五寨等地的民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据文献记载:1621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同时,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瓷器,其中不乏数目可观的的南胜、五寨窑产品,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内外基本销声匿迹。
-----------------
这里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瓷器的图片:
http://www.mydragonsdream.com/antique/ceramics/sell/blueandwhite/blueandwhite16.htm
|
|
|
|
|
|
  共2 页 第1页 (10条跟贴/页) 共2 页 第1页 (10条跟贴/页)
  |
|
|